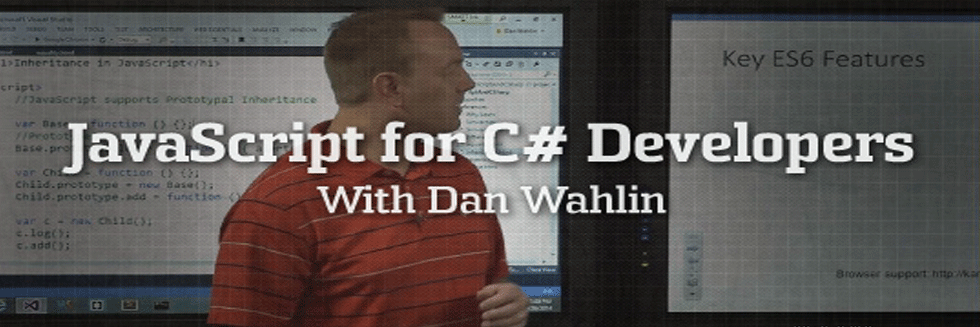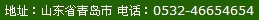|
主谈人 叶橹,原名莫绍裘,著名学者、诗歌评论家,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汉诗界》顾问。在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评论界享有权威地位,诗坛“泰斗”。20世纪80年代,在现代主义诗歌大潮中,叶橹先生以“辩护人”的身份推动了中国先锋主义诗歌的发展,是中国青年诗人的鼓舞者、理论推动者。 采访人 庄晓明:年生于扬州,中国作协会员,九三学社会员,《汉诗界》副主编。已出版作品多部。 李青松:著名诗人。 问:从一开始,您的评论文字便获得了一种坚定而自信的风度,发表于《人民文学》年2月号的《激情的赞歌》一文,谈到闻捷:“一年来,闻捷给我们写出了《吐鲁番的情歌》《博斯腾湖滨》等好多首优美的诗篇,我们有理由这样说:我们的国家又出现了一个有才能的诗人。” 在发表在《奔流》年7月号的《公刘的近作》一文中,这样评论到:“从诗人近年来所发表的诗篇来看,无论在思想内容的深度和艺术技巧上,都在原有的基础上提高了一步……而这,正是公刘以往的诗篇所缺少的。当诗人一旦把这种敏锐的艺术感受能力和对生活的深刻观察。思考结合起来的时候,他的诗篇就放射出耀眼的光彩。” 写这些具有预见性的评论文字的时候,您还是大学中文系的一名学生,我们不能不惊讶于您对重要的诗歌和诗人出现时的迅捷的反应,敏锐的判断。自然,这一切应归之于您对生命赋予自己的一种诗歌使命的确认,请问,您是如何与文学,与伴随了自己一生的诗歌命运结缘的? 答:命运充满了偶然,结缘诗歌也是如此。但对于文学,我可谓有着一种天性的喜爱。上小学时,家中的书,哪怕是写了字的纸片,都会让我如获至宝。中学时期,我开始了广泛的阅读,鲁迅,巴金,沈从文,当时能获得的重要作家的作品都读,尽管有些作品当时并不能完全读懂,但这些名家作品中所营造出来的文学味道,让我甘之如饴。因此,中学时代我就有文章在《广西文艺》上发表了。 年的人民文学 其实,进入武汉大学时,我是从对戏剧感兴趣而写评论的,曾有一篇关于讽刺剧方面的文章,发表在《剧本》杂志上。但年时,发生了转机,当时,我注意到一个现象,《人民文学》连续几期刊登了闻捷的诗,那时,诗歌的主流还流于口号的层面,流于跟风写作。而闻捷的诗歌刚好反之,写哈萨克,写苹果树下,写吐鲁番情歌,写果子沟山谣,确实非常好。于是,我便写出了我的第一篇诗歌评论《激情的赞歌》,寄给了《人民文学》。 年轻时的叶橹(中) 出乎意料的是,编辑部很快就回了信,说你写的非常好,我们会很快编发出来。《激情的赞歌》发表于年2月的《人民文学》,之后,编辑部又和我联系,寄来十几个题目,希望我能够就这些题目写一些关于诗歌方面的文章。收到这样的信,自然非常激动,便选择了《抒情诗中的我》,谈“小我”与“大我”的问题,写了约一万字。半个月后,稿子退了回来,我以为是没写好给退了。展开信一看,大吃一惊,编辑部说,你这篇文章写得太好了,可惜写得太短太少了,你可以再充分发挥一下。 我写文章从来不打草稿,都是大体的思路先定下来,然后一气呵成。这样的写作过程中,总有灵感光顾我,我也会发挥的非常好。我也曾试过打草稿,但往往拘谨了思路的自由发挥,效果并不理想。 譬如,《人民文学》约写的这篇两万多字的《关于抒情诗》所花的四天时间,都是上课之余写出的。文章发表时,是用大黑体字标示的,全国就这么个顶尖刊物,一下子引起了轰动。我的老师程千帆先生也大吃了一惊,为我写出这样的文章感到骄傲。自此,我一发而不可收拾,沿着诗歌评论这条道走了下去。 问:作为武大的高材生,就在您踌躇满志着,考虑毕业后是去《人民文学》,还是《文艺报》工作的时候,一场席卷全国的反右运动,将您和您的老师程千帆都打成了右派,并开始了您不堪回首的近23年的流放劳改生涯。 由一个大学的天之骄子,一下子坠落到如此的炼狱,真不敢想象,您是如何熬过来的? 中国著名古代文史学家、教育家,南京大学教授程千帆老师 答:这可谓我性格的悲剧,我的性格太耿直且刚烈,为胡风集团说了些话,又不会掩饰自己。这种极端的落差当然不是常人所能承受的,何况我当时还是一个未经世事的大学生。那时,武汉长江大桥刚建成,有一天,我独自走到了大桥上,想一跳了之。 可是对着江风的浩荡,江水的不息流逝,我突然想明白了,不可以,一个男人来到世上,不是为了得到这样的下场。我内心狠狠地对自己说,活下去,我倒要看看这个世界,倒底会这么样! 我先是被判刑三年,到硫铁矿采石场劳动改造,习惯了那矿井崩塌,人如蝼蚁,瞬间消逝的惨象。刑满以后,被转入到大黄石新生石料场,这样一来,我的劳动可以按件计酬了。我推板车,把石头推到碎石机里,多推就多得,少推就少得。有一次,在酷暑中,我还在山边捡石块时,突然前面轰隆一声巨响,半边石壁塌了下来,整个儿埋住了沟底下拉石头的几十名留场人员。我的这条命可谓是捡回来的。 问:您的劳改流放时间,加起来约有20年,和同样因为右派身份,被流放西部的大诗人昌耀的时间差不多。而且,您的生活经历和昌耀还有着许多令人感兴趣的相似处,昌耀在荒凉的青藏高原与一位不懂汉语的土伯特女人结婚而安居寂寞;您则在苏北一偏远的乡村与一位不识字的善良的姑娘成家而艰难度日。 你们都是在清算了极左的路线之后复出,并辉煌于诗坛。是否因为这些相似的经历,使得您更深刻地理解了昌耀先生,成为了他的诗歌文本解读的权威?同时,您的评论昌耀的文字,也使您复出后的评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诗人昌耀 答:可以这么认为吧,算是20年苦难的某种补偿。我曾一再这样提示昌耀诗歌的存在,如果我们对这样的诗依然保持沉默而不给以应有的肯定,让岁月的尘垢淹没了它的艺术光彩,或是在若干年之后再让人们重新来发掘它,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应该说是一种批评的失职和审美的失误。从本质上说,昌耀是一个沉思者,他的诸如《慈航》《划呀,划呀,父亲们》一类的诗,皆是可以在文学史上留下来的精品。 昌耀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所写的那些诗篇,我用“峻烈”二字加以概括,就是因为它们具有一种冷峻的热烈。冷峻是其内质,热烈是其外壳。就像一个人长期生活在寒冷的环境里,一旦将他置于亚热带气候中,他最初的强烈感受可能就是温暖;但是即使他对温暖已习以为常,他的内心深处和隐蔽的记忆里,寒冷依然会是最刻骨铭心的感受。 我感受到了昌耀的伟大,其他人却不尽然。我的第一篇评昌耀的文章《杜鹃啼血与精卫填海》,其实就是为他鸣不平的。在年的全国诗集评奖中,我是为《昌耀抒情诗集》写推荐语的人,结果终评时,《昌耀抒情诗集》偏偏被挤了下来,而且是唯一一本被挤下来的诗集,理由是看不懂。 年的“运河诗会”上,我对刘湛秋表达了我的愤懑之情。由于相似的命运遭遇,我是如此早如此深刻地体味到了昌耀的伟大,深重的苦难感和命运感,来自青藏高原的土著民俗元素和大地气质,现代生存剧烈的精神冲突中悲悯的平民情怀和坚定的道义担当,以及“君子自强不息”的灵魂苦行,构成了昌耀在诗艺和精神上对当代汉语诗歌无可替代的贡献。 《昌耀抒情诗集》() 或许,我要感谢我23年的劳改流放的命运,使我与昌耀在精神的脉动中产生了如此的共振。昌耀在苦难生活的那种大寂寞中,依然寻求一种博大容涵的内心世界,乃是一种被外力所强制和扭曲而不得不另辟蹊径的情感宣泄方式。他之所以能在精神上不被摧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获得了这种精神支撑。 尽管这种精神支撑只存在于内心深处的幻想,可是如果没有这种诗性的幻想,他就会在苦难的折磨中日渐变成一个精神猥琐的庸人。这就是一个有诗性内质的人同没有诗性禀赋的人在本质上的不同。 问:但是直到今天,还有许多人认为昌耀的诗难懂,作为研究昌耀诗的专家,您能否给他们一把进入昌耀诗歌的钥匙? 答:昌耀的诗思属于那种潜隐式的诗性思维,现代诗人中,一个废名,一个卞之琳,都具有这种诗思特色。我之所以将昌耀的诗性思维方式概括为“潜隐”二字,正是基于他的令人难以觉察的天马行空和突如其来。他的诗思不是那种按起承转合的方式结构而成,往往是以突兀的方式起句,而后则任情绪之流引向一种散发式的泛滥。这种诗思方式相当典型地体现了潜意识活动的特点。 只要读过昌耀诗的人,一定会对他的这种句式留下深刻的印象,突兀有力的节奏感,似乎隐现着诗人内心一种难以抑制的情绪,同时又呈现着散发式的意象表达方式。它们给人的印象似乎是散漫而零乱的,但又是极具生机与活力的。 叶橹在青海“昌耀诗歌纪念馆”和艾青夫人及骆寒超教授合影 这种诗性思维的特点,不在于引导你循规蹈矩地按某种形式去进入诗境,而是激发你自身的生命活力去充分发挥联想和想象的能力。一些人之所以认为昌耀的诗难懂,除了对昌耀诗的内涵缺少认识之外,很大程度上是对昌耀的那种潜隐式的诗性思维感到陌生造成的。 问:昌耀《慈航》的解读之后,对洛夫晚年巨作《漂木》的解读,是您的诗歌批评的另一高峰。长达三千行的《漂木》,是洛夫先生年逾7旬的伟大诗章,是他一生生命的结晶,于年出版,虽震惊华语诗坛,但尚未有相匹配的诗歌解读文本来支撑它的伟大——对此,打个不是很妥帖的比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再富有创造性,但如果没有其他杰出科学家的观察实验成果来与之相呼应,就难以成就它的坚实的伟大。 而您的系统性的《“漂木”十论》,可谓起了这方面的作用。您能否谈谈与《漂木》的相遇? 《漂木》 答:洛夫在古稀之年为华文诗坛贡献出的长诗《漂木》,不仅是他个人创作上的一个奇迹,也必将是中国新诗史上的一个重大的事件。像《漂木》这样的长篇巨著,不要说一般的读者难以进入,即使是专业的阅读,也需要专心致志的投入,才能收到理想的艺术效果。 诗人洛夫 一部长达三千多行的诗篇,既没有故事的叙述,更谈不上以情节动人取胜,那么,它是靠什么来吸引读者的阅读与审视呢?我反复阅读了《漂木》十余次,认定是它的艺术结构和意象经营方面的匠心独运,造就了它独特的艺术魅力。 第一章“漂木”,实际上是人生流浪游走的纵向阅历和观察的艺术表达方式,它所涉猎的海峡两岸种种社会现象和人文景观的部分,是积郁于诗人心中数十年的忧患意识的体现。它是现实的,又是意象化了的诗性观察。这一章是具有“纲”的性质的一次以纵向发展为脉络的宏观性表达。 《汉诗界》主编傅国栋和叶橹先生在探讨汉语诗歌最新发展 它的庞杂丰富的内涵对《漂木》的成功有着奠基石的作用;第二章“鲑,垂死的逼视”,是一次具象化的借题发挥。是对人的生存状态所作出的极具感性和个性的心理层面的表达;第三章“浮瓶中的书札”所含的“致母亲”“致诗人”“致时间”和“致诸神”诸篇,无疑是一种横向的散发性的人生体悟和寄托。 诗人主要表现和传达出站在人生十字路口或曰在海浪的颠簸中发出的人文信息。他对“母亲”“诗人”“时间”和“诸神”的一系列发言及对话,其呕心沥血的艰辛,苦心孤诣的追求,内外交困的矛盾,乃至相互矛盾的无奈,如此等等,无不真实和真诚地表达一个现代诗人,在面对诸多形而上和形而下的问题时,那种复杂万端又百般无奈的深层次心理活动。第四章“向废墟致敬”,相当于一间贮藏室。 叶橹在他的书斋 在这座“废墟”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历史的遗存。也许其中许多东西对于当今社会现实不一定有实用价值,但它的“痕迹”却是不能从历史中抹去的。这一章在人们面前展示了许多谈不上是辉煌却不乏琐屑的事物和意念,然而,在它那众多的叙述和意象之间,我们却读出了人类生存发展史的真实过程。 诗人的眼中和心里并不是没有崇高和辉煌,他只是忧心忡忡地面对着那些使崇高和辉煌日渐变得猥琐和黯淡的事物。 《汉诗界》副主编、本文作者庄晓明和叶橹在诗歌研讨会 总之,《漂木》可以说是包罗万有,它也许会成为中国现代诗史上一个常议常新的话题,现在人们对它的议论和评说可能才刚刚开始。 未完待续………… 《汉诗界》副主编、本文采访人庄晓明 附-昌耀作品: 《慈航》节选爱与死 是的,在善恶的角力中 爱的繁衍与生殖 比死亡的战残更古老、 更勇武百倍。 我,就是这样~部行动的情书 我不理解遗忘。 也不习惯麻木。 我不时展示状如兰花的五指 朝向空阔弹去—— 触痛了的是回声。 然而, 只是为了再听一次失道者 败北的消息 我才拨弄这支 命题古老的琴曲? 在善恶的角力中 爱的繁衍与生殖 比死亡的戕残更古老、 更勇武百倍。 文字编辑?傅远+Esthr 扫描北京治疗白癜风的地方皮肤白癜风如何治疗
|
当前位置: c#发展_c#学习_c#开发 >诗歌与生命的解读者叶橹访谈上
时间:2017-2-19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2016都快过去了,先放下诗和远方,关心
- 下一篇文章: 净宗法师透视人间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