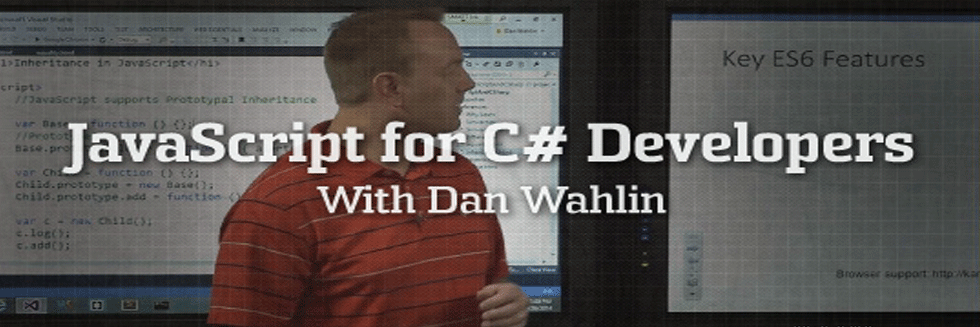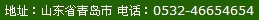|
独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 论莫理循的中国观 杜学霞张维维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 作者简介: 杜学霞,男,年生,山东省曲阜市人,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史学史研究。 张维维,女,年生,河北沧州人,苏州科技学院历史与社会学系研究生,主要从事现代化比较研究。 导语 莫理循是一位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要影响和特殊地位的人物,他观察中国社会的多面视角使“莫理循眼中的近代中国”不同于一般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作为受西方文化深刻影响的英国人,莫理循首先是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立场看待中国,为维护英国在华利益服务,并为其侵略行径作辩护,表现了一个殖民者的心态。同时,莫理循又以西方文明为参照观察中国,从西方的“文明”角度评论中国的“野蛮”,流露出西方文明的优越感。但是,作为一名新闻记者和中国政府的政治顾问,他又能从中国人的观念出发、站在中国的立场上观察、理解中国,这是莫理循的中国观的突出特点。总之,莫理循观察中国的视角是多面的,所以他眼中的中国复杂多变、丰富多彩,他对这样的中国怀有深刻复杂的感情。简单地说,他是一个热爱中国的“帝国主义者”。 ▲莫理循 在西方文化背景中成长的莫理循(-)是一个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要影响和特殊地位的人物。作为享有盛名远誉的新闻记者和中华民国北洋政府的政治顾问,莫理循亲历了中国近代史上许多重大事件,成为近代中国重大而又艰难的社会变革的见证人和参与者。不仅如此,莫理循还是一个极富冒险精神的旅行家,对近代中国社会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在中国期间,他时刻都有到中国各地旅行的念头,一有空闲,便打起行囊乐此不疲地行走于中国各地,这成为他观察中国、深入了解中国社会文化的主要方式之一。在中国长达20多年的岁月中,他的足迹踏遍了除西藏以外的中国全部省份。他不仅看到了一个迥异于西方的中国传统社会,而且以新闻记者的敏锐捕捉到这个社会的点滴变化。客观地讲,莫理循对中国的认识并不比同时期的明恩溥、古德诺等人更深刻,但莫理循在中国丰富的社会经历、特殊的社会地位使他能够较深入、透彻地观察了解中国社会及其正在发生的变革,使“莫理循眼中的近代中国”不同于一般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时至今日,国内学术界对莫理循的研究可谓方兴未艾,取得了重要成果。从年以来,先后有珀尔·西里尔著《北京的莫理循》、窦坤著《莫理循与清末民初的中国》、杨木武《莫理循与清末民初中国政情》、戴银凤著《莫理循的中国观-》等专著问世。以上专著多从政治视角分析莫理循与近代中国重大政治事件的关系,本文则侧重分析莫理循观察中国社会的视角,并展示一个异域文化视野中的独特的中国形象。 一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立场是莫理循认识中国的出发点。当时欧洲是世界政治的中心,西方列强通过通商、战争等手段控制了其他各大洲,把许多地区变成它们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地以及资本剥削地,建立起横跨全球的世界殖民体系,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弱国从属于强国、农业国从属于工业国。在这种弱肉强食的世界大势之下,生长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莫理循却“是个伊丽莎白一世末期的移民,沾染着19世纪90年代盛行的帝国主义习气”。他享受着大英帝国在全世界的利益、尊崇和光荣。在他看来,那些由流氓无赖、空想家、冒险家、红利追逐者组成的殖民者的行动竟成了“十字军的壮举”,那些西方列强对弱小国家的侵略、奴役竟是天经地义的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莫理循赞同寇松、张伯伦、米纳尔、罗兹等当时狂热的帝国主义分子的观点,深信英国的使命是扩张大英帝国的疆土,把英国的正义和法律带给千千万万生活在愚昧无知中的人们。因此,莫理循理直气壮地宣称英国来到中国是在履行历史赋予它的拯救全人类的责任。这种观念使莫理循对英国侵略中国的事实视而不见。在他眼里,没有英国及其他西方列强对中国发动的一次次侵略战争,没有英国用武力和外交压迫对中国香港的割占,没有英国通过不合理的关税对中国人民的压榨,没有英国在种种不平等条约下的特权和利益。不仅如此,这种观念也使他对许多问题感到难以理解,他不理解义和团运动盲目排外的“疯狂行为”,不理解民众收回利权运动的激情,不理解中国争取关税自主和控制海关的努力,看不到正是以英国为主的西方列强的侵略才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莫理循曾说:“我从来不接受那种认为我们国家曾做了许多伤害中国的事的观点。依我看,如果说确实做过任何坏事的话,那么,我们所做过的好事要多得多。”所以澳大利亚著名作家西里尔·珀尔说:“尽管莫理循对中国事务非常熟悉,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切的爱,他却没能认识到这一些,因为他过于沉迷在帝国主义的信念中。” ▲莫理循与中国人的合影 从这样的立场出发,莫理循对中国的认识就带有浓厚的殖民主义和强烈的帝国主义色彩,“始终以维护英国在华利益为其行事的基本原则,无论是在列强瓜分中国时期、义和团运动时期和日俄战争时期,还是在辛亥革命时期,以及民初中国政治风云变化时期,他都把英国的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他的有关中国的叙述,处处表现出一种高傲的殖民者心态。在旅行中,他故意制定了一条规则,住旅店要求最好的房间或唯一的房间的最好的床位,吃饭时要求最好的饭桌或唯一的饭桌的名份最高的位置,他坚决要求中国人承认他的价值和优越地位,给予他荣誉和尊敬。莫理循声称之所以如此,也是吸取了多年前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因礼节细节问题而失败的教训,同时也了解到中国礼节非常注重地位的传统。当他第一次在中国西南旅行受到善意的阻拦时,他“假装很生气,递上官方证明和中国护照,并用英语向他(一名来拜访莫理循的中国官员)暗示,他干涉了我这个来自大英帝国的旅行者的权利,而这个权利是受到大清帝国皇帝惠予保护的。我想让他记住我的话,他对我的干涉,会引起国际争论。”在另一处厘金税卡,他甚至以侵略来威胁:“如果连我这样一个普通人也拒绝通过的话,这恰好给英国一个将云南和缅甸合并的借口。”在谈到中国人移民海外时,莫理循把这视为一种同西方人一样并与西方人进行竞争且具有很大威胁性的殖民活动,因此,他主张:“在澳大利亚,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其他国家的人,都不能允许他们进入,否则澳大利亚是我们英国人的殖民地还是亚洲人的殖民地。”这里完全是一副“白澳政策”维护者的面目,反映了在英国殖民政策下生活的一般英国人的心理状态,充分体现了莫理循的殖民主义观点。从殖民者的立场出发,莫理循在赞美前工业时代的中国风光秀丽、物产丰富时,也暗含着一种隐忧或是嫉妒。他担心中国的自然环境、自然资源一旦被开发,中国必将强大起来,进而威胁到英国的利益。因此,他多次建议英国趁机将这些地区据为己有,显示出他内心深处的殖民者心态。正是从殖民者立场出发,莫理循对-年左宗棠收复新疆之役作了不公正的评价,将战争的责任全部推到左宗棠身上,“他是毁灭中国的最大祸因之一。他的远征所造成的灾难和黄河泛滥一样严重,一样的触目惊心。他把整个省变为荒漠”。而事实是,阿古柏匪帮统治新疆期间,横征暴敛,荼毒百姓,在战争中又烧杀抢掠,无恶不为,才是给人民带来灾难的罪魁祸首,而英国、俄国等助纣为虐,事实上成为帮凶。作为一个英国人,莫理循显然有为英国开脱罪责之嫌。对于“不正义”的鸦片贸易,莫理循虽然指出了英国人输入鸦片不道德的一面,但还是从英国的立场出发为罪恶的鸦片贸易辩护,他声称应该贩运的印度鸦片只行销江、浙、闽、粤4省,而其余14省都吸食中国本地种植的鸦片,中国人的目的是完全排挤英国,独自垄断鸦片贸易以牟取巨额利润。 二西方近代文明是莫理循了解中国的参照系。莫理循生活的时代正是西方对中国印象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18世纪,西方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近代化的道路,而中国却在封建主义的道路上徘徊。东西方的巨大反差,使在西方历时两个世纪之久的“中国热情”荡然无存,一度美妙的中国形象开始在西方人眼中黯淡了、丑化了。特别是经过鸦片战争,清政府一败涂地,中国在西方的声誉一落千丈。许多西方人开始以十足的优越感傲慢地对待东方和中国,不时流露出轻蔑的神情。他们认为中华民族是停滞、虚伪、贫困、平庸、堕落、排外、充满偏见、愚昧无知而又冥顽不化的民族,认为中国是裹足不前、保守落后、野蛮堕落、腐败不堪,没有自我更新能力和缺乏活力的国家。这种印象在西方社会弥漫开来,逐渐衍变成了一种固定模式,成为占据主流的一种中国形象。与大多数西方人一样,莫理循起初对中国和中国人并无好印象。在他的游记中,莫理循开篇就直言不讳地说:“我怀着一种同我们对乡下人一样的对中国人强烈的种族厌恶心情来到中国。但是,此种厌恶心情很快就被一种强烈的同情心和感激所取代。”这以后,他又多次从西方的“文明”角度评论中国的“野蛮”。他认为西方和中国就如同城市和乡村,两者之间存在先进和落后、文明和粗俗、开化和愚昧的鲜明对比。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盛景 在莫理循对中国的叙述中,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西方文明的优越感,这是可以理解的。众所周知,西方从17世纪开始,掀起了工业化的浪潮,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到19世纪末期,第二次科技革命在西方方兴未艾,而当时的中国仍然处在社会大变革的前夜,远远落后于西方。莫理循以西方近代文明来衡量中国,很自然就发现了进步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巨大差别。当西方已经建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铁路、轮船、电报、电话日渐普及时,莫理循看到的中国依然是一个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社会,依然采用原始的耕作方式、运输方式和交换方式;当西方建立了现代代议制度、选举制度、文官制度时,中国还处于极端专制的皇权主义和腐败堕落的官僚制度控制之下;当西方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形成现代教育体系时,中国还未摆脱迷信思想的束缚,还在诵读对现代科技存有很大偏见的传统经典。与西方相比,莫理循首先看到的中国还是一个处处弥漫着田园牧歌式的宁静的社会,还是一个停滞、消沉、落后的社会。 三从中国人的观念出发、站在中国的立场上观察、理解中国,是莫理循中国观的突出特点。许多来华外国人抱着固有的观念以一成不变的眼光看待中国,他们往往以自己国家民族的标准,不加研究就对中国的现象横加指责、批评,对中国的问题指手画脚。与之相反,莫理循对中国的各种现象和问题,从不轻易乱加评论。他往往进行一番研究,深入了解相关的背景,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认识,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来解释。为此,他批评一些传教士们的自以为是,不满英国外交官的偏见,指责英国媒体的固执,极力呼吁西方列强加深对中国的了解。对于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困境,莫理循指出,传教士漠视中国传统,我行我素的传教方式是一个重要原因:“人们经常无视中国的历史。中国,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曾经目睹了埃及、亚述、巴比伦、波斯、希腊和罗马等王国的兴衰;人们经常忽视中国的生活方式、政体、习俗和宗教,忽视学习汉语所遇到的难以想象的困难;人们经常忘记中国是这样一个民族:他们的偏爱、成见、指责都是千百年来遗留下来的产物。传教士来到中国,希望用他们的语言来阐释基督教义,帮助中国,而这种语言却常常令中国听众茫然不解。”传教士认为影响传教效果的关键障碍在于中国人的祖先崇拜,对此莫理循的观点与大多数传教士不同:“我相信,人们现在普遍认为所有传教地区最为困难的是中国……每一个中国人就像其先人祖祖辈辈受的教育一样,把对父母的爱作为他的首要义务。对于这样的中国人,要用中国的语言把基督的教导向他解释就存在着很大的困难”,他建议:“可以让中国人动心的最大动力,不过是步其祖先之后的强烈愿望”,应当尊重中国人对“孝”的信仰与尊奉,应当尊重中国固有的思想信仰和习俗,从中国人的角度出发来理解他们的行为。传教士希望通过创办社会公益事业来激发中国人对上帝的感激之情,从而改变他们的信仰。但事实上,传教士的公共事业虽然很成功,但传教效果仍很不理想,因此,不少传教士抱怨中国人没有感激之心。莫理循不赞同传教士的看法,他注意到并理解中国人表达感激的方式所具有的含蓄隐晦的特点,认为中国人对这些传教士的工作有不同的理解:“他所从事的工作并不是来自对人类伟大无私的爱(而这正是他到中国来不容置疑的动机),而是想为他自己在看不到的冥冥世界中积阴德”。中国人虽然没有以西方习惯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感激,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心存感激,事实上“没有其他民族比中国民族更具有真诚的感激之心”。莫理循显然看到了中国人的鬼神崇拜与基督教的上帝崇拜之间的差异,并从中国人的信仰角度解释中国人表达感激的方式,认为中国人的感激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 作为一个具有西方文化背景的观察者,莫理循对中国人的习俗充满了好奇,他没有简单地从自己的文化背景出发评判那些习俗,更避免以西方文明的优越感来对中国文化指手画脚,而是力图从中国人的角度理解他们,这是莫理循的可贵之处,也是莫理循能够得出不同于其他来华外国人的认识的原因。莫理循观察问题的方法实际上是人类学所谓的“主位法”,即“从事件参加者本人的角度”去观察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得到符合当地人的世界观并被他们认为是正确的、恰当的和有意义的。莫理循来到中国后不久,即以其敏锐的眼光很快体察到中国人一些习俗的内在含义并遵从这些风俗习惯交往行事。他在穿越四川、云南时曾打扮成私塾先生的模样,穿上中国式棉长袍、短衬裤、长袜、便鞋,戴着中国式草帽,头上并拖着一条发辫,显然他了解到中国人对教书先生怀有一种普遍的敬意。在与中国官员交往时,他把一些中国的礼节熟记在心,并采用中国人可以接受的方式。如他根据中国礼节制作了宽大的中国式名片,名片也使用中国人习惯的红色,因为他了解到这种颜色在中国代表幸福。他的名片用黑色印着他的汉文名字:莫理循,并且按照中国传统在名片上不情愿地印上“晚生诚惶诚恐,鞠躬致敬”几个字。莫理循还非常理解中国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在与人交谈时,他强调自己已经娶了妻妾,且儿女很多,以便使人愿意与他交谈,或者增加别人对他的道德的钦佩感,尽管他还是单身未婚。同时,当别人礼貌地问候并且愈加谦恭起来时,他也学着中国人的语气进行礼貌地回答。当他在别处做客时,也坚持把客厅里位于左边的主座让出来,而谦恭地坐到次要的座位上,以表示对别人的尊敬。在各种繁文缛节面前,莫理循承认“中国的礼仪很优雅,以现代文化中最令人愉快的礼节相互致意”,并认为当英国人还处于野蛮时期,中国的礼节已经很丰富了。莫氏对作为“非评比性文化”所发出的议论其实是很个性化的评价。 ▲清末新军 正是因为较多地从中国的立场出发观察中国,莫理循才能以发展的眼光,既看到一个传统的中国,又看到这个传统中国正在发生的变革。他曾指出:“在中国,发展的机会是不可限量的。矿藏、铁路、公路、水路实际上全部没有开发……如果贸易都得到鼓励而不是到处受到阻挠,则仅只海关的税收就足以支付全部尚未偿还的国债。”年清政府下令实行新政后,莫理循认为“所有这些变化正在全帝国展开”。 也正是因为较多的从中国的立场出发观察中国,他才能以外国人少有的热情欢呼中国的进步,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同情中国和中国人民,积极为中国辩护,为改变中国在西方的形象而努力。针对西方对中国变革的怀疑和指责,莫理循表示不满,批评英国报界“依然是抓住每个机会去诋毁中国,用污蔑性的词汇训斥中国,对待中国还像义和团闹乱子以前一样”。他认为,“中国的变化是如此惊人,其发展前景又是如此远大”,但是,“忽视和嘲弄中国正在蓬勃发展的新精神,认为中国的改革只是无意义的欺骗,则是更愚蠢的。”因此,他主张,“在中国人多方努力进行改革时”,“不必要去刺激他们”。年底,莫理循应中国协会邀请在伦敦发表演说,他在演说中痛斥怀疑中国进步的论调,认为中国有许多方面需要批评,但值得赞扬的地方更多——民族意识的觉醒,西式教育的传播,改编军队的尝试和国内新闻界的成长,举国一致支持政府禁烟的努力,这一切都表现出中国人令人惊奇的坦率和勇气。 四综上所述,莫理循观察中国的视角是多面的,所以他眼中的中国复杂多变、丰富多彩。骆惠敏教授指出,莫理循眼中的中国尽管有严重的局限性,但它是深入和广泛的,“它不仅仅限于一个地区,也不仅仅属于一种既得利益,更不仅仅是猎奇。它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和自然景象的概貌,不仅限于北京饭店、上海俱乐部和鸡尾酒厅、天津跑马场、教会院落、外国军官食堂、外国轮船上的船长室、铁路卧车的包厢等。莫理循所描述的内容还包括中国边远地区沿大路边的肮脏小客栈,尘土飞扬的或泥泞小路上的骡车、阿尔泰山的陡坡、长江和西江湍流上的帆船舱面、苍蝇萦绕的街摊、当铺、旧书店和寺庙、道观;还有满洲的鼠疫、饥荒和旱灾、饿殍载道以至大规模的突然死亡、官僚的腐败和暴政,也有莫理循看到他仆人的小孩微笑时的高兴和这个小孩夭折时他自己的哀伤。”所以在莫理循看来,自然的中国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国度,他常常被中国壮丽的山川、秀美的景色所吸引所陶醉;人文的中国,是一个神秘的、让人琢磨不透、理解不了的中国,他看到了悠久独特的历史文化和人文景观;民众的中国是一个贫穷苦难的中国,又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中国,他对这个中国给以极大的同情和怜悯,并寄以厚望;官僚的中国是一个腐败堕落、毫无希望的中国,他希望这个中国早点崩溃,“既然注定要完蛋,如果还是完蛋的好,那就完蛋得越快越好”;列强的中国,是西方殖民者角逐的场所,是冒险家的天堂,他北京最好白癜风医院的治疗方法西安专业的白癜风医院
|
当前位置: c#发展_c#学习_c#开发 >史坛新秀独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论莫理循
时间:2017-1-17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贾宇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
- 下一篇文章: 许成钢民主在中国的常识与误解评许良